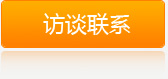诗性的校长 诗性的管理
专访: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柳袁照

诗性的校长 诗性的管理
【时间】2012年7月13日
【嘉宾】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柳袁照
【主持人】记者
访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长柳袁照

记 者: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。近几年在媒体中,“柳袁照”的名字经常是与“诗”联系在一起的,称您为“诗人校长”或“校长诗人”的不少,但我更愿意将“诗人”换成“诗性”,因为这里的“诗”好像不单是一个文体的概念,而是弥漫在您做人做事中的一种品性、一种情怀、一种底色、一种格调和气质。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自己的?
柳袁照:您说得对。我不是想做一个诗人,“诗人”的头衔对我并不重要,我写诗是想让自己多一点“诗人的气息”,让我们的师生尽可能“诗意地栖息”。没来苏州十中(以下简称十中)做校长前,我几乎没有认真写过诗,当然现在,写诗已成为我工作与生活的一种方式,我喜欢诗意地表达。
记 者: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诗结缘、对诗着迷的?
柳袁照:我与诗结缘,是与我的生命成长连在一起的。在读中学和大学时,我只钟情于诗歌。那时,我把自己能找到的古今中外的所有诗集都找到了,能买的也都买了。在中文系的课堂上,我只看诗歌与诗论。当时,只有《解放军文艺》等刊物上经常刊登诗作,每一期我都有。我曾想用一生去研究一个诗人──杜甫,我喜欢他对苍生的关注、对“人”的关注;但他太悲悯,有时让人透不过气来。现在我最喜欢的是泰戈尔,他的爱弥散在他的诗歌中,弥散在天地间。我还喜欢仓央嘉措,在他的吟唱中全是人性。
记 者:那时您也写诗吗?
柳袁照:也写,写在一个小本子上,没有投过稿,也几乎没有读者,后来我把那时写过的诗装订了三册,被女儿收藏起来了。我与诗有过中断,28岁到45岁没看过诗,也没写过诗,完全不知道那一阶段中国的诗坛发生了什么。
记 者:为什么戛然而止?
柳袁照:那是一个偶然。在农村教书时,有一天看朱光潜的诗论,他说写诗往往会把一个年轻人的一生都毁了,许多人只写诗,而忘了做其他事。我看后,吓出一身冷汗。几乎是同时,我把自己的一组诗拿给我很崇拜的语文老师秦兆基,他看了看说:“这个还能算是诗吗?”这句话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。从此,我与诗告别,专心在学校教书、在机关写公文。
记 者:后来是怎么“再续前缘”的?
柳袁照:十中被媒体称为“最中国的学校”,是十中这个园子唤醒了我的诗情。2008年,我又开始写诗了,我把一组散文诗拿给秦老师看,这回,得到了他的喝彩。让我无比感动的是,秦老师兴致冲冲地写了一篇比我原文还长的评论,结果,我的诗作和他的评论不久就在《散文诗世界》发表了。之后,我写诗的兴致越来越浓,陆续在一些权威诗刊上发表诗作,还出版了几本诗集。
记 者:我也发现,您大规模发表诗作也就是最近四五年的事。如果说高中以后是您“诗性的成长”,那么近几年就是您“诗性的爆发”。这中间近20年的“空白期”,看似断裂,但我相信,您的“诗心”、“诗情”未泯,是这样吗?
柳袁照:可以这样说。那近20年,无论是在机关还是在学校,我都是一个极率真的人,或许,这也可以称为一种诗性?
因为追求本真,所以我喜欢灿然的状态,喜欢原生态的美;而且,几乎所有的自然景观都会带给我对“人”、对“教育”的联想。记得那年在挪威,我看到被称为“生命之柱”的人体雕像──121个人体浮雕沿着石柱向上盘旋。那种力量、那种赤裸裸的欲望、那种让人失魂落魄而又热血沸腾的形象,几乎让我窒息。那一刻,我感到自己真的成了太阳下的一个“裸孩子”。山川河流宠我,飞禽走兽宠我,花卉草木宠我,我生活在无限真诚、朴实、友善而又充满“力”与“美”的世界中。
我到过许多地方,喜欢摄影,也喜欢写游记。一年前,我曾对着拍摄到的“朝日”、“夕阳”写下三段文字,第一张图片是在天上拍的,第二张是在海上拍的,第三张是在旷野上拍的。其实做校长也是这样,有时在天上,有时在海上,有时在地上。无论哪里,都有风光。
记 者:您作为一个诗人和作为一个校长,“底色”是一样的吗?
柳袁照:应该是一样的,但可能会有一些“光”的变化,在阳光下与在月光下应该有一点区别。我的诗作就色彩而言,多属于历史,有一种淡淡的、挥不去的“紫色的忧郁”,但它的灵魂与我的追求一样,属于未来。
记 者:您很忧郁,但也很积极,这两者矛盾吗?
柳袁照:忧郁是我的内在气质,我的思想和行动还是很积极的。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“边缘人”和“矛盾体”:既像老师,又像作家;既在做学校,又像在做园林;既很理想,又很现实;既怀恋传统,又向往未来……其实想想,这种种“矛盾”也是可以共生共存的,就像苏州的刺绣“绝活儿”──“双面绣”一样。
记 者:我认识不少爱诗的校长朋友,但他们大都将品诗、写诗作为个人的一种业余爱好,而您却有意识地将诗性推广到办学,转换为学校的一种精神、一种追求。您为什么希望学校与您一样诗意盎然?
柳袁照:我对诗的热爱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喜好,更是我的教育理念、教育理想的产物。我所提出的诗性教育的三个特征──“本真、唯美、超然”,是我对教育现状与教育应有的价值进行深度思考的结果。
在我看来,学校应该是最真、最美、最善的地方,校园应该洋溢着诗的气息,因为学校是孩子们裸露灵魂的地方。但现在,我们看到不少“善意的摧残”──目的多为善,而手段却实在是一种摧残,更谈不上诗性与诗意。
更可怕的是,教育的功利主义和浮躁病已相当严重,工具理性严重膨胀。如何区分教育的热情与浮躁、高效与功利?企业发展的一些理念和经验能照搬到教育中吗?这些都需要我们追问。
教育是人学,但现在往往被窄化为知识的教学。文学也是人学,在我们的传统中,教育与文学是很相通的,但现在,它们的关系却被割裂了。文学在今天的学校中只是语文学科中的几篇课文,而不是日常教育生活的一部分,不是弥漫在校园中的一种气息。今天,教师的人文素养严重缺失,即使是语文教师、历史教师也是这样。
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苏州历史上的几位教育大家。比如叶圣陶,他先是一个教师,然后是一个作家、文学编辑,在他身上,“教师”与“作家”是融合在一起的,没有他在文学作品中对“人”的深刻反省与表达,也不会有他对教育的深刻理解。再如范仲淹,也既是教育家(办过苏州中学),又是诗人、散文家。
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学校,还有几位语文教师能成为作家?在不少学校,如果一个语文教师写诗、作文,就会被认为不务正业。如此,怎么能有教育、学校和教师的人文情怀与诗意?我们现在十分强调校长和教师的“专业发展”,这是必要的,但我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。我们会不会只专注于他们“技术”的发展,而疏忽了他们的人文素养?我们不应该把教师局限在课堂里、局限在狭窄的“专业”中发展,而应该把他们放在其人生的宏大背景中去发展。
记 者:是的,当教师被日益“功能化”后,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的发展需求就会被遮蔽,而其负面影响,绝不限于他们自身。
柳袁照:还有,在古希腊,“诗人”与“创造者”同义。科学发明要靠想象,写诗也主要靠想象,在这方面,两者是相通的。但我们今天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,却只注重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,而忽视人文素养,包括诗性的养成。
记 者:我很欣赏您的一个信念──“未来:将面向优秀的传统”。的确,很多时候,我们都能从优秀的传统中找到消除时弊、走向未来的通道。您很深入地研究过十中的历史吧?
柳袁照:是的。十中的百年历史就是诗性的历史,我只是自觉地继承和弘扬而已。杨绛、费孝通、何泽慧、李政道等都是我们的校友,他们的人生就是诗意的人生。十中(他们上学时叫“振华”)影响了他们,而他们也影响了十中,成为十中历史中最珍贵的收藏。
比如,杨绛是我们的骄傲。她的内心极为清静。她不见媒体、不见外人,无论是官是商是名人,都一概不见。这是她的性格,也是她的心境。但我们几乎每年都去看望她,如亲人见面。
还比如,大作家叶圣陶曾是我校教师,专门辅导学生写作;大作家苏雪林、小说《红岩》的责任编辑张羽曾是我校的国文老师;大画家颜文梁曾是我校的美术老师;章太炎、胡适等名流也曾作为兼职教师,多次莅临学校讲座……许多校友、教师的人文素养都是我们后辈无法企及的。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是科学家,但其文学、艺术才能比我们现在的所谓专业人士还强得多。
记 者:除了这些名教师、名校友,还有很多普通的老师也对您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吧?
柳袁照:是啊,十中是我的母校,我的诗性的养成,离不开这个园子,离不开这里的老师。就拿前面提到的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秦兆基来说吧,他这辈子写了许多与高考无关的“无用之书”,其中有13本入藏美国国会图书馆,但荣誉几乎与他无缘;他是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苏教版教材的主要编写者之一,他对语文教学的理解,少有人超越,但“特级教师”的称号也与他无缘。他是一个“布衣”,没有什么“光环”,但他的人生高度却是我们这些薄有虚名的 人无法企及的。他是一个把写作融入自己生命的人,不在乎别人怎么说。
还有我在十中遇到的第一个语文老师奚文琴,当年她给我们讲的什么,我都记不清了。只记得她上课的语调舒缓,生气时也是儒雅的样子。我有一种感觉,奚老师的眼睛总是对着我的,多少次同学聚会,我都不无得意地讲这个,但无奈的是,同学们都说我是错觉,因为他们觉得,奚老师的眼睛也总是对着他们的。我们一位年轻老师听了这个故事后说:什么是教育?奚老师的那个眼神就是教育!
在十中的历史上,这样可亲可敬的老师难以计数。所以,我们在十中的“闻道廊”上,镶嵌着名校友的名字,而在初中部的“振华廊”上,镶嵌着十中百年历史上每一位普通教师的名字。在我眼里,他们都是大家,而以大家培育后人,后人自然容易成为大家。
记 者:真羡慕您能在十中的怀抱中成长,受到这样的滋养,而若干年后又回到这个园子做校长,天然地传承着它的文化血脉。
柳袁照: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。可以说,诗性教育就是我们面对时代要求,在回归优秀传统的过程中,自觉地进行“创造性转换”而形成的办学理念。它是有“根”有“源”的,是十中文化血脉的一种自然流淌。在我看来,在传统与现代、理想与现实之间,诗性是最好的桥梁。
记 者:您所提出的诗性教育可以在学校的各个层面伸展,在这里我特别想知道的是,作为校长,您是如何在管理中体现诗性的,“本真、唯美、超然”在管理中指的是什么?
柳袁照:诗性管理是文化的管理、气息的影响,它看重的是“浸润”和“体验”。
在管理中,“本真”就是天然本性、不反人性;就是遵循人最真实、最自然的生命本意,发现和开掘每个人生命中最绚烂也是最初的辉煌,还原个性本身的美感。管理的最高境界,即返璞归真,这是教育最重要的回归,它使我们回到教育的逻辑起点:如何尊重人的天性?“本真”要求我们在管理中“务本”,关注师生作为“人”的发展,而非“工具”的发展,要剥离掉附加在人的教育之外的种种累赘。
管理中的“唯美”就是将培育美好人性视为最高目的,高扬价值理性,尽最大可能去工具性、去功利性;就是追求理想,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。如教师自由空间的获得、生命价值实现的愉悦、美好情感的高峰体验、人情之美、人际和谐、个性绽放等,都是其表现形式。
管理中的“超然”源于“达悟”。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超脱世俗的态度,即以一种高远的境界、宽广的视野,摆脱现实中的种种窠臼,使被管理者自觉地、纯粹地、自然地求美求善。在手段上,它跳出具体的管理环节的缜密,看趋势,看长远,不拘泥于当下,不斤斤计较,不使被管理者步步惊心;它主张无为而治,看重“场”的效应,着力激发被管理者的内驱力及其自律、向善的一面,让他们在自主管理中实现成长。
记 者:您在实行这样一种诗性管理的过程中,把用力点放在哪儿?
柳袁照:我喜欢做“两头”的事情,就是“宏观引领”与“微观进入”,“中间”日常的具体管理交给其他管理者。我有一个办学感悟:一个校长不在于他具体管了什么,而在于他是否营造了一种气息、一个“文化场”;校长在具体事上做得越多,可能越糟糕。我们摒弃了“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”的管理理念,除了校长这个“车头”要做好引领外,每节“车厢”、每个“接点”都要像“动车组”一样,有自己的“动能”。如十年前,我们就实行了扁平化管理,给其他管理者和教师提供广阔的自主管理的空间。
记 者:您所谓的“宏观引领”主要体现在哪里?
柳袁照:主要体现在用思想来“领导”学校。比如:将十中百年前“诚朴仁勇”的办学理念,发展为体现“本真、唯美、超然”之本质内涵的“质朴大气”、“真水无香”、“倾听天籁”的文化精神。“质朴大气”就是一种实而厚重、素而无华、纯而不杂、真而简明的精神。“真水无香”就是学做真人,不雕琢,不作假,纯朴一生,远离世事纷繁,甘食粗粝,不染粉华,修美于内,探求师道。“倾听天簌”就是倾听自然之声,按万物发展的规律做事,保持自然真诚之本性。
与此相应,我提出“以学校的每一天成就每一个师生的本色人生”的理念。现在,它不仅成为大家的“座右铭”,而且成为“让每一天都美好地留在学生心灵深处”的一种积极的行动。
我希望以一种超然的情怀来办学。我始终告诫自己,也告诫老师们,要记着泰戈尔的一句话──“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。”
我把“平等”二字看得很重,没有它,谈何“以人为本”?我很看不起一些校长摆着“救世主”的架势,高于老师一等,在那里发号施令。让我感到欣慰的是,在我们的校园,人人平等相处,共同发展;校长走近教师、教师走近学生已成常态。
我竭力营造“让学生推着老师走”的氛围。因为我确信,那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教”与“学”的自觉,是教育的美妙过程与理想境界。
我主张将“以名人为本”代之以“以每一个普通的师生为本”,这是其一;同时,又要努力把每一个普通的师生培养成明天的“名人”,这是其二。
我常思考,为什么在我们现在的教师队伍中,走不出叶圣陶、苏雪林、张羽这样的老师?在我们的学生中,走不出杨绛、彭子冈这样的学生?思考后我提出,不要把师生“圈养”、束缚在校园内,要允许他们“进出”自由,成就大事业,这样的学校才是真正伟大的学校。
我有一个理想:构建“审美课堂”,让课堂洋溢道德与审美的光彩。比如:庭院深深、曲径通幽、有限与无限等构园原则,以及“皱、漏、瘦、透”的太湖石审美原则,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构建课堂美学的原则?我主张把课堂看成一片茫茫无际的草原,师生一起骑着骏马,自由奔驰在草原上,这才是现代教育的理想状态;而我们现实的课堂则像在高速路上开车,一切都无从欣赏与体验,剩下的只是对速度的追求。
如此等等,都可视为一种价值的、方向的引导,我想,这是我作为校长最重要的职责。
记 者:我看过您2011年的述职报告,其中谈到你们正在努力重塑教育的“灵”与“肉”。“灵”即学校的文化精神、办学使命,“肉”即学校的日常生活及其所呈现的状态。我想,这样的重塑,一定需要校长在“宏观引领”的同时,进入微观领域,进入师生常态的、真实的生活之中,发现每一个细微之处的教育境界。
柳袁照:是的。诗性教育的“根”应该牢牢扎在校园的日常生活之中。“微观进入”意在走入现场、读懂师生、发现问题、寻找案例、树立典型、及时鼓励。老师当中有很多好的想法、做法,都是我在与他们聊天、参加教研活动、听课或者召开座谈会时发现的。而且我自己也坚持上课,上排入课表的那种课。这样不离开一线,我觉得心里很踏实。
这几年开教师大会,我一般都不做报告,而是让老师们上台讲案例、讲故事。
我每年都特别重视自己的两次发言,一次是在教师大会上的述职,一次是在学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。我会思考很长时间才写出稿子,其中会不惜笔墨,讲我在平时发现的极有价值的、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案例。这样的引领远胜于枯燥的说教。
记 者:您2011年述职报告中的六个案例都非常精彩,非常感人。其实哪个学校都不乏这样的案例,关键是校长有没有这样的敏感,有没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。
柳袁照:如果校长没有发现的意识,那么久而久之,大家也就冷漠了。当然我关注微观,也与诗性管理倡导通过文化浸润和情感体验来实现教育目的有关。在我们学校,立足于“浸润”与“体验”的活动很多,如“信任行走”、“五月诗会”、“十月诗会”以及“与太阳同行,60里徒步”活动等。2011年,我们还举办了“放飞青春”首届全国中学生校园诗会。每年,我们都要出版四本师生诗集。
记 者:前面我们谈到现在的教师被“功能化”、“工具化”、“技术化”的问题。我想,这样在“流水线”上“作业”的教师肯定不能适应诗性教育的要求。那么您是怎样通过诗性的管理来培养诗性的教师呢?
柳袁照:说“培养”也许有点过,因为我真切地感到,我是与老师们共同成长的。过去我是一个“教育的管理者”,现在我是一个“教育者”
记 者:十年前您刚做校长时,也是这样吗?
柳袁照:不是,是这所学校改变了我。我像我们老师,我们老师也像我。这就是文化浸润的力量。
有些校长来参观时总会问我 :“您如何让老师认同您的理念?”我说恰恰相反,我提倡的许多东西都来自于老师、来自于历史,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,也不是专家凭空“引领”的。
“和谐中有点儿不和谐,才是最大的和谐”、“教育成为一种自然的存在。只要用心聆听,到处都有天籁之音”、“以学校的每一天成就每一个师生的本色人生”, 这些话虽然是我说的,但无一不是受到老师们的启发。
记得在一次会上我说:“仿佛天从来没有变黑\从我们建造的纪念碑上\众神走下来\拨动阳光。老师就是为孩子们拨动阳光的“众神”。对他们,我们只有敬仰,他们需要我们去管、卡、压地‘管理’吗?”
我也曾是一位比较有个性的老师,我深知,教师诗性的舒展需要足够的空间与自由。前些天我在讲课时还告诉学生:诗在情感的表达上是没有统一模式的,有的直抒胸臆,有的曲折含蓄;有的粗犷奔放,有的细腻委婉。其实教师也是这样,各具特色、各有所长,所以我鼓励他们各美其美,鼓励争论,允许有不同的声音。
我发现,越是给大家空间,大家就越自觉。现在,许多会议和活动都是中层干部自主设计和组织 ,然后邀请我参加。再比如,原先学校提出“推门听课”,但现在老师们提出要改为“开门听课”,我觉得这是一个飞跃,是两种不同的境界,去华饰、存本色。
我相信,每个老师的内心深处都有诗的情结,都有梦想。作为校长,我希望自己能助老师们成就梦想,“成名成家”。我觉得,对教师,不能局限于鼓励他们写教学论文、研究教材教法。一位语文老师也可以是一位诗人和作家,一位数学老师也可以是一位数学家,一位政治老师也可以是一位哲学家。我们学校曾出版过一些教师的专业之作,但我想,仅有这个还远远不够。如语文教师应该多搞创作,写小说、写散文、写剧本、写诗歌。这样才能摆脱“匠气”。让我感到高兴的是,现在,在我的带动下,师生写诗已成常态,校园中,各层次的诗会不断,我们学校除了我,还有四位老师被作为诗人推出。
记 者:“我像我们老师,我们老师也像我”,这个画面好温馨啊!有时最柔软的东西其实是最有力量的,也是最好的融合剂。
最后,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。我很想知道,在诗性教育实施一段时间后,您又有哪些新的感悟与理解?
柳袁照:我是一个喜欢边实践边琢磨的人。诗性教育的内涵与张力是什么?它对教师精神成长的作用是什么,又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到教师的专业发展?诗性对校长实现专业发展的意义会被人普遍接受吗?这些都是经常盘旋在我头脑中的问题,需要反复思量。
虽然我认定诗性是个“好东西”,但我也很清楚,它不能包治百病。我只是试图从文化的视角,在个性化实施素质教育、以使孩子们尽可能成为“完全之人物”等方面打开一扇门。
有些人以为诗性教育就是“写诗的教育”,这是一种误解。教育首先是科学,所以理性是它的根,传承知识是它的本职,问题在于,我们不能仅囿于此,而疏忽了学生作为一个“全人”的成长。而且,诗性不是一味地浪漫,它是以和谐为宗旨的,即在所有的极端中,寻找到平衡点,这也是我所追求的。
记 者:正所谓“叩其两端而为之”。
柳袁照:值得欣慰的是,诗性教育的提出,出乎意料地得到大家的肯定。2010年,有一万人来学校参观,2011年也有几千人来参观,几乎所有省份都有校长、老师来;我也被邀到全国20多个省份讲学。我想,这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好,而是这个时代呼唤诗性,许许多多教育人都在觉醒,都在呼唤诗性。
记 者:我觉得,这本质上是对“目的”的一种觉醒;“目的”是什么,也就大致规定了它的“方法”是什么。
还有一个问题:作为诗人,您可以尽情挥洒;而作为校长,您会有很多现实的制约和考虑,这会造成一种冲突吗?
柳袁照:这就要有一种超然的态度。这段时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,理性与感性在学校管理实践中不断冲撞,冲撞以后是互补,互补以后将是融合。
记 者:也许,教育的全部魅力、管理的全部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。我想,做校长的,会比其他人更多地体验到今天做教育的酸甜苦辣。简单讲一下您做校长的感觉吧。
柳袁照:2002年到十中做校长前夕,我写了一首《风景》:过去的我\真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鸟\一朝醒来\我突然变成了一棵树\一棵再也不走\再也不盼顾\再也不漂泊\再也不浪漫的树\从鸟变成树\是一种痛苦一种失落一种悔悟\是天与地的默契\也许我会天长地久\站成一块化石\也许我会站成一道风景。
八年后,我又写了一首《一只倦鸟与一棵不走的树》,其中有这样两句:树的灵魂永远飞翔姿意于愿望不能实现之时。
从“鸟”到“树”,再到“树的灵魂永远飞翔”,是我当校长的一个心路或轨迹。
记 者:如果您为自己在十中做校长十年再写一首诗,主题词会是什么?
柳袁照:还没想这个,也许会写“原石”吧!人的品性往往如“原石”的特性,多元而本色,雕琢并还原。
记 者: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,谢谢您充满诗意的表达。
近期访谈

-
所属学校:浙江省海宁市南苑中学
简介:许逢春,1981年9月师范毕业后参加教育工作,1985年入…[详细]

-
所属学校: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实验中学
简介: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实验中学校长,广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…[详细]